民俗学,又被称为“日常学”,其学科起源与民族主义、浪漫主义等思潮紧密相关,同时也是对抗启蒙主义的产物,因此天然具有反抗性、在野性。作为关注普通百姓生活日常、生命常态的学科,民俗学被赋予民族性、历史性与文化性,甚至提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学科内外的巨大张力源于其深描琐碎日常与宏大话语叙事之间的悖论。
然而,中国的民俗学史通常遵循大历史的分期,以朝代更替的政治史观切割学科史实。现代中国民俗学的起点习惯性地被定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上,但一旦突破辛亥革命这一节点,会发现前后社会思想意识存在内在连续性,现代中国民俗学的发端期可能值得商榷。
自鸦片战争以来,在民族危机深重求变的语境下,随着Folklore的引入、进化论的译介和新史学的倡导,古语“风俗”、“民俗”和“礼俗”被赋予了民族性、国家性以及传统文化、文化遗产等现代意涵。邓实、张亮采和胡朴安等人倡导“风俗学”,形成了被视为中国民俗学经典的《中国风俗史》和《中华全国风俗志》。
如果注意到清末以来“风俗”一词的现代性自我革新,那么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民俗学的起点在内发性层面,至少可以前推到一九〇二年,甚至可以追溯到国学保存会推崇的明季清初顾炎武的风俗观。也即,现代学科意义上中国民俗学是与晚清新史学同步展开的,这使得现代中国民俗学运动具有浓厚的史学属性与民族性。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美国社会学家、民俗学家孙末楠以民俗学说为核心的社会学说引入中国,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成为研究阵地。在此前以周作人为中心偏重文学的民俗学和以顾颉刚为中心偏重史学的民俗学主脉之外,演进形成了“社会学的民俗学”或“社会科学化的民俗学”这一支派。
燕大社会学系师生对民俗学的研究,不仅有着社会学、人类学的主动加盟,同样是其内发性发展的必然。顾颉刚、江绍原、杨成志、钟敬文、娄子匡等人在这一学术自觉的历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此外,杨堃、黄石、吴文藻、李安宅、赵承信、黄迪等人的工作也基本在既有的民俗学学术史视野之外。
对于人文色彩厚重的中国民俗学而言,燕大社会学实验室平郊村的研究,夯实了中国民俗学的“社会学的民俗学”这一流派,实现了民俗学向社会科学的转向。同时,燕大社会学系师生对村落社区的持续观察、调研,使得其本土化演进从“风俗”到“民俗”再到“礼俗”的交错更替。
然而,在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民俗学的社会科学化过程中,其“盲区”与“黑洞”被忽略,尤其是卢沟桥事变后,在民俗学与社会学合流与合力下的燕大“社会学实验室”平郊村长达近十年的研究。尽管这些研究在当下被提及,但并未在燕大社会学和更广博的中国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的学术图景中给予整体性关注。
燕大社会学与民俗学的交汇,不仅体现在学术理论的融合,更在于其对于传统与现代、乡土与都市、小我与大我之间关系的深刻洞察。费孝通、吴文藻等人的工作,不仅推动了民俗学的社会科学化,也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
然而,对于个体、学科甚至人类而言,记忆与遗忘是如影随形的。在《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中,尼采提到:“对于一个人、一个社会和一个文化体系的健康而言,非历史的感觉和历史的感觉都是同样必需的。”
或许,正是这些被遗忘的记忆,才构成了我们历史的一部分,提醒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图片保留
注释: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来源: 《读书》2021年第6期
关注: @文以传道
转载请注明来自察右中旗汇霖节水灌溉有限公司,本文标题:《岳永逸:为了忘“缺”的记忆:社会学的民俗学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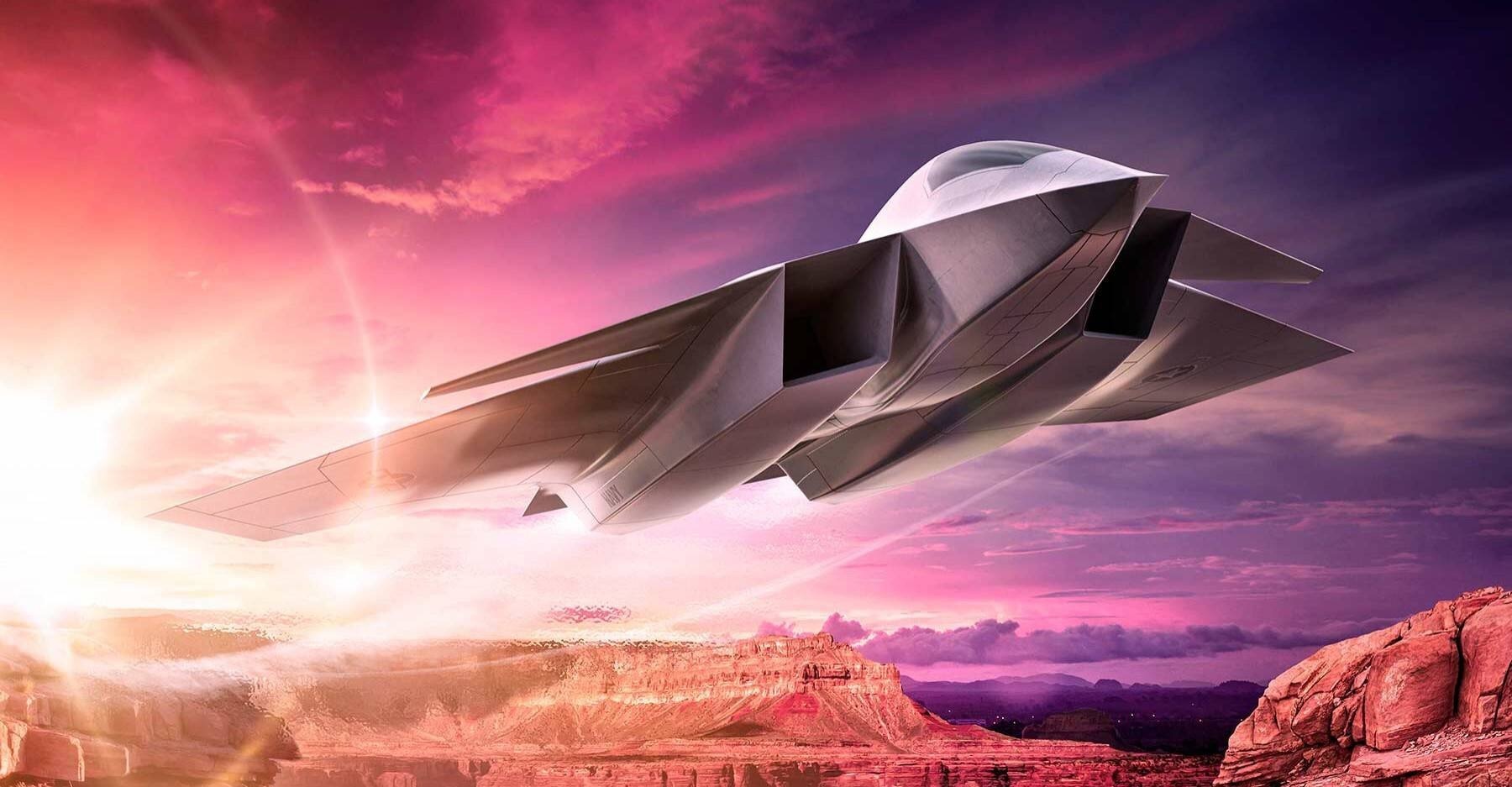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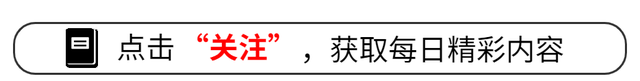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